|
手机影院在线看最热影视 https://www.shoujisp.net 网易娱乐专稿3月1日报道(文|张晶)最近几年,关于张玮玮的文字少之又少。今年年初,网易云音乐出品了他的单曲《2020》,正式宣告张玮玮暌违十年的新专辑要来了。 疫情降临的这两年,每个人的生活都悬浮着,无法落地。 但是张玮玮却在那个疫情的春天复苏了。他想明白一些事。 过去20多年,他执着地追求,总有一天我们会看清生活,实现最牛逼的自己。我们自认是生活的主角。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生活里跑龙套。 张玮玮趟过了那些内心动荡的岁月。 卡顿的人生 2018年底,张玮玮做了一个决定。 他停掉了所有的演出,中止了半生漂泊,住在大理的一处山脚下,日日远眺窗外的山和湖。 那一年,他将自己清空,清空地很彻底,几乎一整年都无所事事。人生的出口尚未找到,很多事都处在一个剧烈的转折期。 就连音乐都提不起他太大兴趣。以前拿着吉他弹一弹就什么都忘了,但是那两年,吉他也弹不进去,弹出来的东西又总是循环,重复,再循环,再重复。 睡眠也不太好,常常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张玮玮觉得自己就像CD卡碟了一样,一直卡在某个地方。 有些东西在张玮玮心里一直过不去。这其中就有父亲的离世。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告别。 “前两天还在医院,他坐在那你跟他聊着,你觉得什么事都没有,最多俩礼拜就出院了,”但是,两天后父亲就走了。 18岁离家闯荡,张玮玮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离别,唯独没经历过生离死别——这是一场真正的告别。 “你突然发现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控的,所有关系都是脆弱的,都有可能随时离开你。” 危机一下子笼罩了他,很多情绪在他心底蔓延。 生命不再是年轻时候不管不顾的状态,也不再是他在《米店》里唱的那样“变成了烟”。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具体,好像一个原本离他很遥远的终点,刹那就出现在面前。 过去20多年,他执着地追求,一定要留下惊世骇俗的作品,总有一天,我们会看清生活,实现最牛逼的自己,透彻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但是,回过头来一看,“自己都已经40多岁了,剩下的时间,我怎么向全人类证明我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很严肃地对自己发出了灵魂拷问。 数了数,没多长时间了。想到这里,内心一阵泥泞。 2020年的春天 2020年初,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疫情的阴霾中。每个人都见证者人类的一段特殊历史。 一切都静止了,“如同刚出土的文物那样凝固”。 张玮玮原计划正月初五北上排练,但是疫情一来,排练延期了。这个春天,大家都不上班。 他和母亲被“困”在了大理。从18岁离家至今,他第一次和母亲共同生活了四个月。母亲每天给他做小时候的吃食,用张玮玮的话说,就是各种“碳水大集锦”,但他的体重居然还降了3公斤。 早上起来,节拍器一开,张玮玮就开始练吉他,中午被母亲叫下去吃饭,吃完饭午睡一会起来接着练,隔一天就陪母亲出门暴走,从早上一直走到日光当头。 老人爱看连续剧,张玮玮听那个声音有点崩溃,他就给老太太推荐《权力的游戏》。万万没想到,母亲看到第二季就看嗨了,看完整季的《权游》,其他美剧继续安排上。 那段时间,张玮玮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拥有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生活。那些疙疙瘩瘩、不畅快的东西,在母亲柴米油盐的细碎生活里,一一消散了。 从那以后,张玮玮好像重生了,浑身倍儿清爽,如同早晨打开窗户,吹来的第一股凉风。 早两年,张玮玮还处在表达自我的焦虑里,身上残存着一些文化人自恋的臭毛病。 但是那四个月的浸润,他慢慢能听进去别人说话了。现在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和滴滴司机聊天,两个陌生人交换着各自的秘密,大家在这短短的半小时里彼此交付,谁都不用对谁负责。 张玮玮说,很多时候,我们自认是生活的主角,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生活里跑龙套。 “向全人类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这事儿,还是算了吧。没有了“主角”包袱,生命一下轻松了许多,像从一个故事里跳了出来。 乡愁,朋友 张玮玮已经三年没回过白银了。 在张玮玮的音乐路上,白银于他,仅仅是一个匆匆过客。现在的白银完全是陌生的,他的乡愁不在那里。 白银是个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那里独特的矿产资源,吸纳了一个时代的劳动者。 1976年,张玮玮出生在这个小城,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像个世外桃源,带着几分“乌托邦”色彩。 他的父亲是一名音乐老师,沉默寡言。每天晚上家人围着火炉烤花生,父亲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摆弄乐器,用蓝色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五线谱。那个背影在他后来的生命里时常显现。 父亲对小儿子寄予厚望。于是张玮玮被逼着学音乐,日日在老师温暖的手风琴声中沉沉睡去。 为了克服昏昏困意,他去跑圈,用凉水洗脸,也没少挨父亲的打,但都没能让他清醒。 老师找到父亲说,这孩子可能不是学音乐的料。父亲的脸阴沉了几天,他的音乐启蒙就这样结束了。 但后来,张玮玮遇见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友郭龙,用他的话说,让他的音乐梦彻底变异。 两人的相识颇有些戏剧性。第一次见面,是看到郭龙在路上打架,他一边打一边说,“你记住,我是郭龙。” 路过的张玮玮暗暗地说,这个郭龙太可怕了,离他远点。 结果开学第一天就被他截了。第二年就成了朋友。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他们都迎面赶上了急剧变化的时代,工厂没有了,整个社会像翻书一样,飞快地变幻着模样。 他和郭龙在当地白银饭店一楼的舞池里,在五彩斑斓的灯光和烟酒气里,诞生了自己的摇滚梦。 两个年轻人离开遥远荒凉的白银,变成了招摇过市的文艺青年,北上南下,漂泊半生,结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在他乡寄托着乡愁。 相对于故乡,朋友在张玮玮心里显得更加重要。年轻时没少跟郭龙吵架,两个人相互刺激,什么狠话都说过,但是现在坐一起,说出来的话都觉得“肉麻”,“就想着怎么把对方夸一顿。” 他退出所有乐队也跟这个有关。“谁不想永远在一起,但是只要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就必定带来痛苦。” 所以,不要寄托太多东西,我们现在不唱悲伤的歌。 走远的“白银饭店” 张玮玮在大理住了小十年,近两年有些倦了,去年3月,他离开了大理。 从大理搬出来后,张玮玮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上海,心怀安宁地站在这个节点上,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重回闹市后,张玮玮正在筹备他的新专辑。距离上一张专辑《白银饭店》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十年过去,张玮玮觉得自己老了。 前两年还和朋友喝大酒,逮住青春的尾巴死死不撒手,大家都梦想再活五百年。如今,这些执念也逐渐淡去。 他丢弃了那些虚无的、莫名的包袱,只想做一个“称职”的民谣歌手。 现在能勾起张玮玮兴趣的只有三件事:学合成器,看《街舞》,与滴滴司机聊天。 2018年演出暂停以后,张玮玮放弃了过去的乐器,他的手风琴被遗忘在了某个角落。 张玮玮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合成器上,为此,他特意购入了一台1971年产的红色合成器,比他年纪还大几岁,请了一位专业的制作人,每周上一节课,课后要完成作业。 “整个合成器的正弦波是怎么变成各种音乐的,所有声音是怎么构成的,有点像物理课。”张玮玮说,他要“彻底、全面地开发合成器”。 他认真摆弄乐器的样子,像极了当年坐在桌前抄五线谱的父亲。 最近几年,他最爱看一档综艺《这就是街舞》,他的抖音号关注了14个跳街舞的,喜欢的原因是“所有人都干干净净,认认真真把自己最牛逼的活儿亮出来”。本质上,他们都是手艺人。 张玮玮的几个爱好,看似没有关联,但是细细分析,他所有的兴趣都映衬着他的变化。 2022年年初,他发表了自己的最新单曲《2020》,用一个故事,讲述他在疫情时期的感触。 张玮玮说,人总要经过那些自恋自大自负的时刻,迈过去,把它们全部踩在脚下,扫进垃圾桶,才能收获一个更开阔的自己。 又是一年三月,朋友圈又响起了《米店》里“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而张玮玮的“白银饭店”已经走远,留下的只有“不重要的那两个角色/跑龙套没有悲伤/你戴着两层口罩我眼镜起了雾/我们就这样走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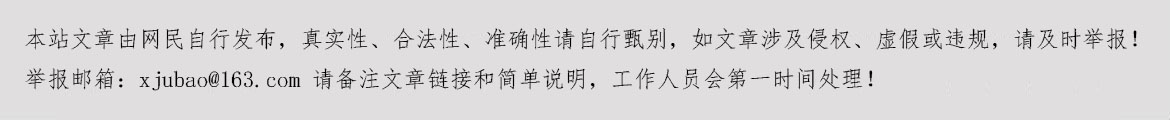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 新闻资讯
• 活动频道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