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EX英雄 http://www.917dg.com/list_10/6969.html 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摘要近年相继颁布实施的某些绩效评价与管理文件存在逻辑瑕疵,新近的财预[2021]101号文尤其典型。该文按“成本-产出-效益-满意度”分设一级评价指标的做法,明显地混同了评价对象、评价要素与评价标准,导致绩效信息的不良分类与含混不清,进而产生误导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践的高风险。回归“投入-活动-产出-成果-受益-影响-满意度”的结果链逻辑模型,把一级指标按其逻辑重要性分设和并列为成果指标(包括衍生指标)、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拒斥不合逻辑的任意发挥,才能消除混乱并产生最适当的绩效评价信息。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背景下,确保以最适当的绩效信息评价绩效至关紧要。 关键词项目绩效结果链模型绩效指标正确分类101号文 前言 题为“关于印发《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的通知》的财预[2021]101号,再次触及一个值得费心思量的重大主题:如何建构适当的绩效指标评价公共支出绩效。中国是典型的支出大国。目前四本预算的支出总额超过经济总量(GDP)的45%。但规模本身不能说明公共支出的价值。公共支出的价值只有通过绩效才能得到检验与证明。准确评价公共支出绩效因而至关紧要,涵盖支出总额绩效、支出配置绩效和支出使用绩效。101号文针对的是公共投资项目(建设或运营)的支出使用绩效。 与少被关注的总额绩效与配置绩效评价相比,项目绩效评价一直被作为重点而受到特别关注。相关政策文件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绩效指标上,101号文也不例外。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绩效指标的适当性决定绩效信息的适当性,进而决定绩效评价的整体质量。不适当的绩效信息不可避免地误导和扭曲绩效评价,无论事前、事中还是事后评价。绩效评价被误导或扭曲,意味着对公共支出成败得失的判断可能出现重大偏差,这会招致诸多负面后果,包括误导决策制定与执行,最终损害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关切的目标与利益。 为确保绩效指标的适当性,相关政策文件应基于非常明确合理且含义精确的理论框架。不是说文件本身要提出和阐述理论框架,而是说文件所设计与规定的绩效指标不可任意发挥,以至信马由缰地完全脱离合理框架的约束与引导。“理论指导实践”之所以特别重要,正是因为缺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深具盲目性,从而大大降低成功概率。 以此言之,不难发现101号文的瑕疵十分明显:绩效指标的设计全然脱离结果链逻辑模型(理论框架)的约束与引导,几近任意发挥到不合逻辑的地步。该文把“成本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并列为四类一级指标,并据此规定相应的二级指标。这种看似正确的绩效指标分类实际上存在严重偏误与含混不清,导致无法产生正确分类的绩效信息,而“正确分类”正是确保绩效信息适当性的关键前提。不良或错误分类不可能带来适当的绩效信息,因而无法保障绩效评价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正确分类”的特殊重要性一直被严重低估,在实践中误导绩效评价与管理的风险很高。101号文对绩效指标的不良分类相当明显:把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与评价要素混杂起来,根源则在于脱离结果链模型的任意发挥。 一、分清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与评价要素 评价对象回答“评价谁的绩效”:投入绩效、产出绩效还是成果绩效?任何特定“项目”的“项目绩效”都涵盖这三个基本评价对象。其他相关的评价对象,比如利益相关者、经济、社会、环境、行为(扶贫项目影响穷人的行为),都由整个项目或其基本评价对象派生而来。举例来说,在评价污水处理项目的成果(水质提高)时,需要考虑受益群体及受益分配,还要考虑对周边环境、餐饮业和房地产业的影响;前者属于受益评价,评价对象是项目成果受益者;后者属于影响评价,评价对象为“环境”和“经济”(产业)。受益评价和影响评价都由成果评价拓展或衍生而来,作为对成果评价的补充评价,因为单纯的成果评价不能充分说明项目的成败得失。 为避免明显的不合逻辑和差错,设计绩效指标的文件首先需要回答最基本的“指标问题”:什么应被评价?也就是明了绩效评价的对象或客体。成本不是评价的对象,而是特定评价对象的要素或(财务)维度,101号文却将其并列于作为评价对象的产出,这是明显的逻辑混乱。在逻辑上,成本与评价对象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缺失基本的可比性,如同“血压”(评价要素)与“人体”(评价对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无论特定组织还是特定项目,支出绩效的“基本评价对象”只有三个:(1)投入评价,从“购买”项目投入角度看待项目绩效;(2)产出评价,从“生产”与“交付”项目产出的角度看待项目绩效;(3)成果绩效,从“实现”项目目标的角度看待项目绩效。101号文把“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与“产出指标”并列,同样属于典型的逻辑混乱,因为效益和满意度属于回答“评价什么”的评价要素问题,而非“评价谁”的评价对象问题。这类错误,与把血压、体温等评价要素与“人体”(健康)并列起来的错误类似。 概括地讲,“绩效指标”的正确且良好设计必须清晰区分三个层次的问题: 评价对象:谁/什么需要被评价? 评价标准:用什么规范作为评价尺度? 评价要素:特定标准用什么维度或内容评价? 效益、满意度和成本都是至关紧要的绩效信息,但问题不在于绩效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这些重要的绩效信息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项目投入的绩效、产出的绩效还是成果的绩效?无论绩效信息多么重要,只要与正确且紧要的评价对象脱节,便失去了其实质意义。“正确且紧要的评价对象”首先是成果(outcomes)、其次是产出(outputs)、最后是投入(inputs)。 成果直接联结政策目标,因而也是决定整个项目成败得失的关键和终极依据。成果还为政府行为和组织行为提供导向,得以成为绩效管理的合理目标。更一般地讲,成果是结果导向(result-orientation)绩效管理的核心和基石,101号文却匪夷所思地将其漏掉了。试图用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取代成果徒劳无益,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效益、满意度和成本回答“用什么进行评价”,成果回答“什么需要被评价”;前者属于评价要素,后者属于评价对象。 就项目绩效指标设计而言,首要的是确定“究竟什么需要被评价”(评价对象),其次才是“用什么标准评价”(评价标准),最后才是“用什么要素或维度说明评价标准”(评价要素)。一般结论是:建构绩效评价指标必须遵循“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要素”这一正确次序,并且不可将三者混为一谈。101号文把四类一级指标并列起来典型地属于“混为一谈”:成本、效益与满意度同“产出”之间,成本与效益之间,以及满意度同其他三类一级指标之间,都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在逻辑上无法并列对待,101号文却“硬生生地”将其武断地并列起来。 绩效文件本应去除模糊混乱以利指导实践,但101号文反而制造了许多逻辑混乱。绩效指标建构的正确逻辑如下: 首先确定评价对象:综合投入、产出、成果绩效评价项目绩效 其次确定评价标准:综合投入的经济性(economy)、产出的效率(efficiency)和成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项目绩效的评价标准 最后确定评价维度:用财务维度的要素(成本等)和非财务维度的要素(数量、质量与时效等)证实或证伪评价标准 项目支出绩效“四类一级评价指标”的正确分类如下。 101号文中的成本指标属于财务维度,数量、质量与时效属于非财务维度。将这些指标与产出指标并列完全不合逻辑:成本属于评价要素,其真实作用在于说明投入的经济性、产出的效率和成本的有效性。成本与产出(以及投入与成果)的关系,典型地属于从属关系而非平行的并列关系:成本是产出绩效的关键方面,正如血压是人体健康的关键方面。把成本与产出并列,如同把血压与人体并列一样不合逻辑。更一般地讲,成本、数量与质量表达“绩效属性”,而产出表达“绩效主体”,两者在逻辑上无法平行分类,而且根本不具有可比性。101号文将两者混同起来,不仅反映逻辑混乱,势必招致实践误导。 二、成本指标作为二级指标才有意义 101号文把成本指标作为一级指标,旨在突出成本信息在绩效评价和成本效益分析中的重要性,改变由来已久不重视成本评价和缺失成本信息的局面。然而,重视成本信息是一回事,如何规定成本指标以确保收集“适当的成本信息”是另一回事。把成本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对待,意味着把成本信息同产出、效益和满意度进行切割,使成本信息成为抽象的、孤立的、与成本对象缺失关联的信息。这样的成本信息即便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也无法作为绩效评价的“适当信息”使用,从而大大降低其有用性。 不妨设问:假设已知其个特定项目的“项目成本”为1000万元,这个水平究竟属于偏高、偏低还是适中? 这样的设问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抽象的“项目成本”概念本身就没有意义,除非它与“谁(哪个项目)的成本”以及“什么(投入、产出还是成果)的成本”联结起来。举例而言:某个人“某天花了1万元”属于偏高、偏低还是合理水平?这并无意义,因为它没有联结具体的成本对象:一吨饭?一件衣服?还是别的? 毫无疑问,“项目成本”(无论多高)是至关紧要的信息,因为它为制定项目预算与概算提供了客观基础。但如果没有说清楚它究竟指项目的“投入成本”、“产出成本”还是“成果成本”,这个“客观基础”就是虚幻的,因为无论多高都无法给出任何适当评价。 对任何水平的“项目成本”而言,只要未与投入、产出、成果或其他成本对象(比如活动)相联结,我们就无法说清它究竟偏高、偏低抑或适中,也就是说,这样的成本信息在绩效评价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而全然没有意义。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成本信息必须作为归属评价对象的二级指标对待才能有意义。101号文把成本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因而没有实质意义。毕竟,成本水平的合理性属于相对概念,只有相对于特定成本对象(及给定数量与质量),是否合理才能得到适当说明。 就特定项目而言,特定成本对象有三个基本层级:项目的投入成本(购买与使用环节)、产出成本(生产与交付环节)和成果成本。抽象的、作为一级指标对象的“项目成本”既没有联结投入、更没有联结产出与成果,因而属于没有意义的成本信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同“血压100”这个信息没有指向人、大象或别的具体对象一样,全然没有实质意义:无法说清它属正常还是异常。 把成本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对待还直接招致第二类错误:把成本信息从产出(以及效益)绩效指标中移除。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缺失了表明“代价多高”的成本信息,产出绩效评价就是不完整的:即便产出数量、质量、时效等非常合意,也无法说清给定数量、质量、时效的成本水平是否合理。由此可知,对于任何给定的成本对象而言,数量、质量、时效等非财务评价必须与成本评价联系在一起,彼此不可分割。无论如何,在最低限度上,任何一项产出(以及投入与成果)都必须一并使用“数量-质量-成本”这三个核心要素进行绩效评价,人为地把成本从中切割出去的做法都意味着重大遗漏和不充分。在这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罔顾成本谈论产出的数量、质量或其他任何东西,虽然并非全然没有意义与价值,意义与价值也势必被大打折扣。 作为一般规则,数量、质量、时效或其他非财务绩效评价,必须与财务维度的成本评价一并使用,因为成本水平是否适当,只有相对于给定数量、质量、时效等非财务要素才有意义,无论评价的是项目的投入绩效、产出绩效还是成果绩效。101号文把成本指标当作一级指标而与产出(以及效益与满意度)指标并列,导致产出评价完全脱离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由数量、质量、时效等信息给出的产出评价,远不足以说明产出绩效是否合意:合意性只有在比较“得”(数量与质量等)与“失”(成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 只有把成本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对待,逻辑混乱和实践误导才能避免。“二级指标”意味着成本信息与投入、产出、成果等成本对象建立了联结,也与每个成本对象的数量、质量、时效等非财务要素建立了联结,从而能够回答“谁的成本”和“相对于什么(数量、质量、时效或其他)的成本”。这样的成本信息不再是孤立、绝对的和抽象的,而是有了具体实在的评价对象和参照物。项目绩效评价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成本信息。 诚然,项目成本作为一级指标并不妨碍下设二级指标:投入成本、产出成本、成果成本或其他(活动等)成本。但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产出成本难道不是“产出指标”吗?评价产出绩效的指标难道只允许使用数量、质量等非成本指标吗?这是怎样的逻辑? 既然产出成本在逻辑上和常识上都必须作为评价产出绩效的关键维度,那么,把成本指标从产出指标中移除就站不住脚,而且可能带来招致两类重大遗漏的高风险:在产出评价中遗漏成本评价,在成本评价遗漏产出(成本)评价。高风险还表现为两类重大重叠:既用产出指标评价产出(数量与质量等),又用成本指标评价产出(成本)。 这种既重复又遗漏本身就代表不合逻辑的错误分类或不良分类。满足“既无遗漏又无重叠”的分类才是合乎逻辑的正确分类,并在贴近目的时形成良好分类。101号文对绩效指标、进而绩效信息的分类,明显地不满足良好分类的两项基本要求:合乎逻辑、贴近目的。不良分类很普遍,其深远负面后果一直被低估与忽视。指望不良分类带来良好(绩效)管理是不可能的,特别在一级分类上。一级分类的错误代表起点错误:首步出错,步步出错,其混乱、模糊与相应的负面后果在后续环节中被不断传递、累积与放大。如果不从源头上加以矫正,情形就是如此。“项目支出”(预算)和“基本支出”(预算)的分类,也是此类例子。 成本信息对于评价与管理所有成本对象都很重要,无论投入、产出还是成本,抑或把投入和产出结果在一起的活动(activities)。“项目成本”也只是在联结项目的投入、产出、成果或活动时才有意义。如果某个项目的“项目成本”为1000万元(或者其他任何数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除非表明其指向性:项目投入(购买)的成本?项目产出(生产与交付)的成本?项目成果(实现)的成本?抑或项目活动的成本? 由此可知,把“成本指标”作为一级指标了无意义。当我们使用支出使用层面的“绩效语言”时,必须明白一个常识:绩效或者“项目绩效”,只有在联结“投入的绩效”(经济性)、产出的绩效(效率)或者成果的绩效(有效性)才有意义。成本要素和其他(产量与质量等)要素,也只有与投入、产出、成果联结才有意义。原因简明有力:成本要素和其他要素都是相对的。 除了使用数量、质量等非财务要素进行评价外,项目的投入绩效、产出绩效和成果绩效亦须一并使用成本信息进行评价,否则将不能说明问题,至少因存在重大遗漏而无法充分说明问题。以此言之,把成本指标从产出指标中切割(并列)开来实属重大瑕疵。 尽管项目的“投入成本”信息对制定预算与概算非常重要,但就绩效评价与管理而言,唯有联结产出与成果的成本信息才有意义。即便某个项目极具经济性(成本节约与高性价比)或者不存在浪费,如果没有合意数量与质量的产出,那么,该项目的投入成本也没有意义;即便某个项目极具产出效率,如果没有实现目标成果,该项目的产出成本的实际意义也会降低。 从根本上讲,一个项目是否值得花费(多少)成本,并不取决于完成该项目的建造或购置需要“购买”与使用多少投入(人力与物力资源),而是主要取决于该项目实现目标成果(联结政策目标)的可能性,其次取决于可产生与交付目标产出的可能性。这与结果导向绩效管理的核心理念完全一致:评价与管理绩效,首先必须以成果说事,其次必须产出说事,最后才以投入说事。“说事”指“言说绩效故事”。重要性的正确逻辑次序必须是“成果-产出-投入”。 反观101号文可知,一级指标并非以“成果-产出-投入”及其衍生指标分类,而是以明显不合逻辑的“成本-产出-效益-满意度”分类:看似正确,实则严重背离基本逻辑。“基本逻辑”要求桥归桥、路归路:是评价对象(成果、产出与投入)的归评价对象,是评价标准(经济性、效率与有效性)的归评价标准,是评价要素(成本与数量等)归评价要素;三者不可混为一谈。“基本逻辑”还要求体现绩效联结的紧密度:成果与绩效的联结最紧密,产出次之,投入最弱。权重设计也要体现这种重要性排序。 “基本逻辑”也要求所有项目的投入、产出和成果评价,都应包含成本评价。101号文一方面正确强调了成本信息在绩效评价中的特殊(一级)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合逻辑地把项目分为两类:设置成本指标的项目和不设成本指标的项目。这等于在政策上允许许多项目绩效评价无需评价成本。既然如此,成本信息的重要性和普适性又如何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不言而喻,成本信息对于所有项目都具有大致相同的重要性,因为任何项目绩效概念本质上都反应“得”与“失”的比较。不设成本评价,如何能够评估“失”?没有“失”的考虑,如何能够约束评价者去比较“得失”?没有基本的得失比较,又如何谈得上(完整)绩效评价? 成本核算历来是一个难题,但核算和评价项目的“投入成本”的难度相对较低,至少在原则上应规定适用所有项目,而不应网开一面。考虑到权责发生制会计已经应用于公共部门,规定所有项目应核算和评价产出成本也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并且至关紧要。相对于投入成本信息而言,产出成本信息更有价值。在公共组织中引入作业成本法(ABC)并率先应用于某些试点项目也很重要。 在产出成本核算大致准确可信的情况下,将相关产出的成本归集于特定成果从而形成“成果成本”信息,难度也将大为降低。就与绩效的联结程度而言,或者就帮助评价项目的成败得失而言,成果成本信息比产出成本信息更重要,产出成本信息比投入成本信息更重要。无论如何,“项目成本”信息至少应以投入成本表达,鼓励扩展为产出成本和成果成本信息。网开一面的做法势必削弱对成本信息的关注,这与把成本指标作为一级指标对待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效益过于笼统且无法取代成果与影响评价 正如言明的那样,101号文把效益指标与成本指标并列为一级指标的意图相当明显,那就是支持成本效益分析。但问题在于:把绩效评价目的与绩效决策目的混为一谈,本身就反映了工具与目的错配。不同的目的需要匹配以不同的工具。工具本身的正确性和适当性取决于目的:有怎样的目的,即应有怎样的工具;目的不同,工具也不同。 101号文化的主要目的是绩效评价,因为文件从一开始就言明项目支出绩效目标针对“通过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同时规定“绩效目标通过具体绩效指标予以细化、量化描述”。既然已经通过预算安排,剩下的问题就不再是决策制定问题:哪些项目纳入预算是可行的,以及如何决定优先性排序。“决策制定”的两个关键方面分别是“可行性”和“排序”,成本效益分析正是与之匹配的分析工具。 在决策制定问题得到解决后,接下来就是执行层面的“绩效评价”问题。决策与评价属于两类明显不同的目的,尽管存在关联。决策是决策,评价是评价。决策决定项目的可行性和择优(排序),评价决定业已完成可行性论证和择优的项目在实施环节上的成败得失。与决定“谁入围”和“谁优先”的决策目的不同,绩效评价目的是鉴别项目实施的成败得失;前者适合采用成本效益分析作为通用工具,后者适合采用结果逻辑模型作为通用工具。这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成为共识和常识。 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101号文把原本服务于决策目的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支持这一分析的“成本指标”和“效益指标”,作为绩效评价的核心工具(一级指标)使用。这是典型的工具-目的错配,势必导致“成败得失判断标准”的严重紊乱。 绩效评价回答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判断某个项目成功或失败的标准是什么? 正确答案肯定不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效益是否大于成本。正确答案来自“目的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实现”。实现目的就代表成功,没有实现目的就代表(某种程度)失败。结果导向绩效评价的核心原则简明扼要:以结果论成败,或者“主要看结果”。结果(results)的核心是与目标成果相对应的实际成果,目标成果直接联结项目追求的政策目标。举例来说:如果政府水务政策目标是“提高水质”,这项目标约束污水处理项目的目标成果与之保持一致,比如“3年内使本地80%的工业污水经治污后达到3级水质”。达到此目标表明成功,没有达到就表明某种程度的失败,无论污水处理项目的总成本是否高于总效益。 进而言之,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不能作为鉴别项目成败的依据,充其量只能作为参考。项目成败的主要依据必须是成果及其有效性: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原定目标成果,即与政策目标一致并受其约束的计划成果。101号文把成本指标与效益指标作为评价项目成败的依据,不仅不合因果(工具-目的)逻辑,而且会削弱对政策目标的关注。作为结果导向绩效评价的一般规则,判断项目成败的核心依据必须是政策目标是否如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而不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 结果链模型最适合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它把重点放在“结果”上,采纳“主要以结果论成败”的立场;同时把“成果”作为结果核心和基石(结果还包括受益与影响),采纳“主要以成果论结果”的立场。由于成果在逻辑上被严格要求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结果链模型引导绩效评价与管理聚焦“政策目标”本身。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而是政策目标是否、多大程度上如期实现! 就绩效评价而言,效益是否高于成本充其量只是评价成败得失的“参考”,远非“依据”。把“参考”混同为“依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类比的是:父母的意见本应仅仅作为“是否与他(她)结婚”(决策)的参考,却被误作决策依据,将会发生什么?或者本应仅仅作为评价“婚姻成败”的参考,却被误作评价的依据,将会发生什么? 即便对于决策目的,成本效益分析的适当角色也只是“参考”,因为决定某个项目是否“纳入预算安排”和优先性排序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效益是否高于成本,而是政策重要性,尽管“参考”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与结果很重要。政策重要性集中体现在联结政策目标的“成果”指标上,而不是宽泛的成本指标和效益指标及其对比上。 成本效益分析取代成果指标作为评价绩效的依据,不仅意味着用错了工具,还会导致绩效评价与管理偏离正确焦点:政策目标约定与约束的目标成果及相应的实际结果。无论公共项目的类别、规模与性质如何,结果导向概念约束公共组织与官员聚焦政策目标,而不是成本效益,尽管成本效益信息对决策支持至关紧要。偏离政策目标的项目几乎可以一票否决,无论其成本效益如何。 政策目标不仅反映理想和决心,更反映可信与可靠,而可信度与可靠性依赖“有效性=实际成果/目标成果*100%”加以验证。这就是结果导向绩效评价与管理的核心逻辑和立场,经由结果链模型集中表达。这如下成本有效性理念完全一致:公共组织与官员应致力以更低的成本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成果比其他任何绩效指标都更紧密地联结政策目标,包括成本指标和效益指标。结果导向绩效评价与管理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成果,包括联结政策目标的目标成果、对应目标成果的实际成果,以及由两者结合而来的“有效性”,或者一并考虑成本(分母)的成本有效性。 没有人会质疑成本信息与效益信息的重要性,但就绩效评价与管理而言,政策目标和目标成果重要得多。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政策把成本效益作为“政策目标”对待,只有追求财务盈利目标的项目(极少)例外。综合政策如此,部门政策也如此。综合政策主要是跨部门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追求经济政策的三个一般目标:增长(蛋糕做大)、平等(蛋糕分享)和稳定(皆可持续)。部门政策指教育、医疗、科技、环保等特定政府职能领域的单项政策。 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公共组织主要通过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涵盖综合政策和部门政策。每项政策都有其相应的“政策目标”。绩效管理提供“把资源配置与政策目标联结起来”的框架、程序与工具,绩效评价则作为其中的关键一环。政策目标通常相当昂贵,需要花费公民和纳税人的许多金钱,关注、鉴别和公开其成败得失因而至关紧要,也反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核心诉求。以此视之,绩效评价的相关文件理应约束与引导机构与官员聚焦政策目标,并将政策目标转换为公共项目的目标成果,进而主要依据实际成果与目标成果的比较(有效性)评价项目与政策的成败得失。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通过特定项目加以实施。 “项目”概念本身就是“政策实施”的同义词。如前所述,这些政策目标与相应的目标成果,不可能是宽泛的成本效益,因而也无法由成本指标与效益指标表达。以此言之,101号文把绩效评价的“正确焦点”引向了错误方向:把机构、官员与资源配置的焦点从政策目标和目标成果移向“成本效益”。这是一种相当有害的导向。考虑到公共政策融合了治理者、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切的利益与目标,焦点漂移尤其如此。 不得不说,成果与效益是两个完全的概念。在成本效益分析语境下,效益通常指经济、社会、环境等维度上的收益(相对于成本)被转换为货币收益。转换技术虽然有多种选择,但总的来说相当复杂与粗糙,许多非货币项目(如监狱建造与管理)甚至无法被适当转换。相比之下,政策目标和目标成果完全无需转换为“效益”:需要的只是“准确鉴别”和计量。因此,以成果指标评价绩效简单实用且有效得多,而且更契合多数机构与官员的专业水准和行政能力不可高估的现状。 四、回归结果链模型的因果逻辑 基本结果链模型的逻辑正确性毋容置疑,并且在全球范围内经受长期的时间考验。模型本身也具有技术中立性,无涉“姓资姓社”。更重要的是,结果链模型非常质朴易懂,贴近客观实际,以至缺失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士也能理解,但若被任意(不合逻辑)发挥,则另当别论。 质朴易懂集中反映为两个基本绩效理念:有投入必有产出,否则暗示资源浪费;有产出必有成果,否则就不能说明是否达到目的。两者由基本结果链模型即“投入-产出-成果”表达:起点是投入,投入绩效由经济性表达;终点是成果,成果绩效由有效性表达;产出则是把投入(花钱)转换为成果的桥梁,产出绩效由效率(投入产出关系)表达。经济性、效率和有效性并称3E,分别作为评价投入绩效、产出绩效、成果绩效的标准,层层递进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分明:项目绩效在起点上表现为不存在浪费(经济性),在中间(建设或运营)环节上表现为投入产出效率,在政策目标或项目成果上表现为有效性。经济性是基本要求,效率是更高的要求,有效性(达成)目标是根本要求。 相对于成果所表达的“结果”而言,投入和产出都代表“原因”。成果的绩效层级最高,因为它是评价项目成败的关键方面;产出的绩效层级次之,投入的绩效层级最低。如果成果不佳,那么,结果链模型要求把原因追溯到投入和产出上,比如投入不足、投入浪费或与产出缺失联结,或者产出的选择不当以至没有瞄准目标成果。这种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为项目(和组织)评价其运营绩效不可逾越的正确逻辑,一旦逾越它,绩效指标与绩效信息就立即变得“说不清道不明了”。101号文正是如此。 不可逾越并非指结果链模型不可灵活变通,而是说灵活变通必须合乎逻辑:把结果和引起这些结果的原因清晰区分开来,确保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并且原因与结果之间形成紧密联结以剔除噪声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噪声指与“管理”无关的不可控的干扰因子,与管理因子共同影响结果,因而作为影响评价的关键一环。天气状况(风向、风力和降雨等)即为环境质量(结果)的常见噪声因子。如果结果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噪声的影响,那么,管理努力和资源投入的意义何在? 下图呈现了结果链模型的“正确逻辑”。 上图呈现了完整的结果链逻辑模型,用以评价组织或项目层面的运营绩效,即区别于支出配置和支出总额的支出使用绩效。受托责任(为人民服务)要求一线机构与官员对投入组织或项目的资源承担绩效责任:计量投入绩效的经济性、计量产出绩效的效率、计量成果绩效的有效性。“投入-产出-成果”因而构成结果链模型的“基本部分”,因为其他的评价对象皆由其组合或衍生而来:活动(作业)由投入和产出组合而来,成为建构绩效指标最适当的微观单元;受益(benefits)和影响(impacts)则作为成果的衍生评价,用以辅助或补助说明成果的有效性。 由此可知,就建构支出使用绩效的一级评价指标而言,分设和并列(1)成果指标、(2)产出指标、(3)投入指标以及(4)衍生指标才合乎逻辑并贴近目的,因而可产生“正确且重要”的绩效信息;相比之下,(1)成本指标、(2)产出指标、(3)效益指标、(4)满意度指标的一级分类显得不伦不类,无法产生逻辑上正确、实践上贴近目的的适当绩效信息,以至不能提供项目成败的准确且充分判断。 成本指标和效益指标取代“成果评价”和“影响评价”尤其容易导致评价结果的扭曲和失真。把成本指标分设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把效益指标分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指标,虽然就成本效益分析而言目的或许是适当的,但与影响评价的含义与逻辑格格不入,并且就绩效评价目的(区别于辅助决策)而言并无实质重要性,充其量只是“参考”。实质重要性集中体现在成果(有效性)上,其次是产出(效率)和投入(经济性)上。 与受益评价(公平性equity)和满意度评价一样,影响评价也是对成果评价的衍生评价,涵盖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涵盖鉴别和剔除噪声对成果的影响。影响评价要求鉴别影响的程度(高中低)、性质(正面与负面)、方向(上中下游产业)以及持续性,但并不要求估算具体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从而可大大降低绩效评价的困难、复杂性和工作量,进而也可大大降低扭曲和失真程度。就一线机构与官员的整体专业水准和行政能力现状而言,要求估算外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影响的成本与效益,明显地不切实际,强行推之很可能适得其反。相比之下,影响评价既合乎逻辑,也切合实际,但101号文反而将其忽略。一并被忽略的还有成果与受益。对于扶贫等再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诉求相当明显的项目而言,忽视受益评价更是难以理喻。受益评价特别关注低收入或穷人的福利,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项目实施的影响。 结语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许多部门出台了大量关于绩效评价与管理的政策文件,对推动“全面绩效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真正重要的并非文件的数量,而是文件的质量。1个高质量的政策文件,好过100个甚至更多低质量的政策文件。就评价项目绩效的绩效文件而言,严格遵循基本结果链模型表达的正确逻辑,拒斥不合逻辑的任意发挥,才是高质量的可靠保障。以此言之,101号文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亟需后续的修订与完善。 (结束。2021-09-08) 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出品 网易研究局是网易新闻打造的财经专业智库,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于上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针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财经智库。欢迎来稿(投稿邮箱:cehuazu2016@163.com)。 移驾微信公号看这里看不到的内容 【精彩推荐】点击进入网易研究局·中国版>> 【精彩推荐】点击进入网易研究局·国际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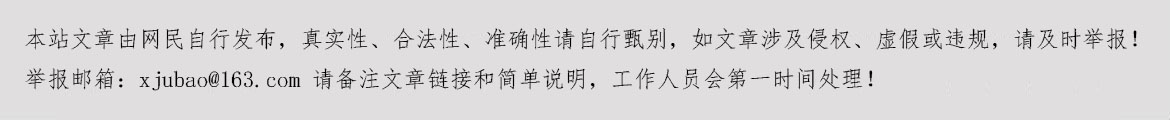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 新闻资讯
• 活动频道
更多




